他曾对秦昭王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
-朱汉民:中华文化里面,有些能够与现代生活对接,有些就不能够。有些政治上向往自由、民主的近代士大夫,内心也真诚地信仰儒家的圣人之道。

要达到整个世界的和谐,不需要建立一个超越信仰,人道就具有天道的意义。我的切身体会是,与同事一起工作,价值观确实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西方企业管理研究的成果。国学也需要加以辨别,但是不应该成为一种担忧,为此而拒绝弘扬国学。我曾经遇到某汽车公司销售老总,他告诉我,他的销售原则就是仁义礼智信人类在两千多年前轴心时期所创造的人文经典,那个历史时期留下的人文价值理念,包括怎么做人、怎么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怎么建构一个和谐合理的社会等一些涉及道德、审美、信仰等人文精神的内容,仍然是今天人们的思想源泉。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超越学派,从中华民族无限丰富的典籍里,为现代中国人构筑精神家园、为中华文明复兴、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来建立新的经典体系。回归经典并不是目的,而是要重建中华经典学,或者说是重建现代新经学。近代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政治思潮,都表现出对经济均平、政治平等等大同理想的特别向往,这种相同的思想推崇,和其推崇者身上具有的士大夫传统有关。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诚能够为人所认知与实践,实现反身而诚。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所以我们倡导士大夫精神,也就是希望当代中国的社会精英们能从士大夫精神传统中,获得他们特别稀缺的人格精神力量、道德表率作用。湖湘文化精神有一个特点,就是湖湘士大夫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养成。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曾国藩对理学的钻研是勤奋、躬行的。二程则主张主敬、穷理、寡欲。

曾国藩强调: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新民学会取义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革新学术,砥厉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又进一步确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学会宗旨。湖湘文化与士大夫精神 记者:近世湖南士大夫不只是曾国藩,其他如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是不是也都下过这样的苦工夫?湖湘文化精神中是不是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养成? 朱汉民:是的。这些人的精神气质影响到后来的数代湖湘士大夫与知识群体。
许多文化精英,也不是把自己作为优秀文化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反而是精神文化的摧毁者。推动西方社会近代化过程的是新兴的市民阶级,他们追求的是其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的精英人物,也就是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郭嵩焘认为:办天下事只是气,气盛则江河直泻,才虽小,亦乘势以飞腾。
张载的四句教对后世士大夫的道德完善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希望实现孔子讲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完成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圣学传承、天下安泰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他立志要从事于克己之学,并且严格按理学家的要求,修身养性,潜心于义理之学,以求在人格修炼上有所成就。

所以,士志于道是士大夫精神及其人生哲学的根本。湖湘士大夫的理想人格,体现出圣贤与豪杰相结合的特色。
杨昌济辅导他们以理学的修身工夫论。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化理想和道德操守,体现出圣贤的价值追求、人格修养,又有坚强的血性气质、卓越的军政才能,在风云变幻的近代历史上显出独特的精神风范与人格类型。但是,中国的近代化恰好是由士大夫群体来推动的,他们的思想动机、奋斗目标似乎不是源于其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而主要体现为士大夫精神中的救国救民的经世情怀和圣贤—豪杰的人格理想。譬如,他反复强调诚是人的立志躬行之本,人的诚自何来?曾国藩一方面坚持认为诚是人心中所本有的天理、寂然不动之体。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起,曾国藩开始记日课,希望念念欲改过自新。为实现慎独的修养境界,他总是自觉地去其好名利之心、无恒之弊,以及克服自己的忿气、懈怠、玩忽之习,总是在不断地自责和反省中,防微杜渐,不放过任何小事,持之以恒,最终铸就了自己的道德人格。
我们希望,通过学习借鉴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找回古代的士大夫精神中这种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气魄。气苶则百端阻滞,虽有长才,无所用之。
这和西方的近代化思潮有非常明显的差别。为什么宋代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在今天还能够被很多精英人物重新提倡,就在于这种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精神境界,能够弥补我们现在的一种精神缺失,能够开阔很多人的胸怀。
但是,湖湘士大夫强调做事必须以做人为基础,主张将圣贤的价值理想、文化理念与豪杰的意志能力、经世事业相结合。他还主张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本来,圣贤所代表的是一种对儒家理念的坚定信仰、对儒家道德的身心实践、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推广。什么是士大夫精神? 记者:您的一篇演讲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在微信朋友圈曾经很火,您在演讲中提出中国古代丰富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其实都是士大夫精神的表达和追求,在您看来,建构士大夫精神的人生哲学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朱汉民:士大夫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学者—官员型的社会阶层,由于这个士大夫阶层既经营学术文化又从事社会治理,故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士大夫人生哲学。比如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不是用公共权力来服务人民,而是满足个人的无穷利欲。日记里说,他这一次去主要是请教检身之要和读书之法。
他们将士大夫在人世间追求理想的仁道,看作是引导、完成人类参与天地宇宙的生生不息的过程、目的和意义,最终形成了士大夫所特有的参天地,赞化育的人生哲学和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气魄。中国近代的政治理念为什么和西方近代的政治理念有很大区别,应该说与士大夫作为近代化运动的主体有关系。
曾国藩按照慎独的要求,在待人接物中自觉地内省改过。到了宋代,理学的修身工夫论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周敦颐力倡主静、立诚、无为。
曾国藩强调,诚意以致知为知识基础与前提条件,他倡导明宜先乎诚,他通过自明诚的阐发,表明学问工夫的明最后会体现于诚中,学问积累与人格修养的方法因此获得了一种一致性。如他与人久谈,过后会反省而觉得不妥,即所谓多言不知戒,绝无所谓省察者,志安在耶?耻安在耶?他看人作应制诗而应酬性地当面夸奖,他回头也会自责不忠不信,何以为友。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去拜访唐鉴,唐鉴传授的修身工夫论给曾国藩莫大的启发。但是,您认为士大夫精神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依旧存在,并且依然影响着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一百多年前,科举制度废除了,原来意义的士大夫不能作为普遍化的社会阶层而存在。故而,作为社会精英,一定会在当时的社会思潮、道德风尚方面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
第二年,曾国藩又向另一位理学大师倭仁请教修身工夫论。学会对会员的道德修养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强调会员必须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
清末废科举,后来又经历了革命,作为社会阶层的士大夫不再存在。曾国藩是理学的实践派,他的最大特点是遵循这一套工夫论认真扎实地去实践。
记者:您倡导的士大夫精神应该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如何修炼自己的士大夫精神? 朱汉民:士大夫精神其实是一种精英文化。张载讲穷神知化、存诚、大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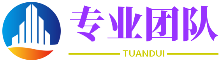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